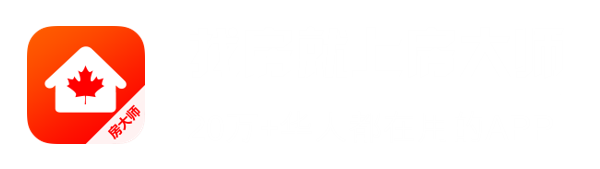“中产阶级”长期以来是加拿大各大政党竞选时频繁提及的关键词,几乎所有党派都承诺要为中产减税、提供经济支持。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选民群体,大多数加拿大人也认为自己属于其中。

然而,这一概念对加拿大年轻一代而言,正变得越来越模糊。曾被视为中产生活象征的“拥有住房”“定期度假”等指标,如今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已经遥不可及。
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(OECD)将“中产阶级”定义为年收入介于税后家庭收入中位数的75%至200%之间的群体。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数据,这一范围约在52,875至141,000加元之间。
但对许多年轻的打工族来说,达到这个标准仍是难以企及的目标。
现年35岁的护理专业学生奥佩耶米·克欣德(Opeyemi Kehinde)正在全职读书的同时,每周工作20小时,并与丈夫一同养育五个孩子。她的丈夫是一名地质学家。她说,她心中的“中产阶级”只是意味着“在不领薪水的情况下,家庭能坚持生活两周”。而他们的家庭,目前连这一基本门槛都难以达到。
“我们连基本生活都几乎负担不起,”她说,“每天都在祈祷不要遇上紧急情况,不要生病,也不要失业——因为我们根本承担不起这些风险。”
他们一家在2022年从埃德蒙顿搬到安大略省康沃尔,希望生活成本更低。但租金依然高涨,他们不得不从整栋出租屋搬进一个三居室的公寓。她表示,去年全家总收入不到4万加元,而房租已涨至每月1,880加元,两个月的电费账单高达800加元。
她也试图通过多工作几小时来增加收入,但这反而会增加托儿费用,而且没有可靠的夜间或周末托儿选项可供选择。
更具讽刺意味的是,如果她的收入稍微提高,可能还会失去现有的低收入社会补贴,“努力工作”反而成为一种惩罚。
中产阶级:定义模糊,标准下移
2023年《加拿大阶层研究》显示,约42%的加拿大人自认为是“中产阶级”,另有17%认为自己属于“中下阶层”,还有17%属于“中上阶层”。
阿尔伯塔大学社会学教授、该研究主导者之一米歇尔·马罗托(Michelle Maroto)指出,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本身就非常模糊,尤其是对年轻一代而言,其传统意义已难以适用。
“对老一辈来说,中产意味着有房、有车、有养老金、有假期。这些对很多年轻人而言,现在都是难以实现的。”她表示,疫情以来的经济形势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代际分化。
她呼吁,政界应推动更具进步性的税收制度,用于重新投资公共教育、医疗和住房,“这样,才有可能重新点燃年轻人迈入中产的希望”。
“我们之所以越来越远离传统中产生活方式,是因为最顶层的1%在收入和财富上的拉升幅度,远远超过了社会其他人。”她说。
“中产”不再意味着买房:年轻人只求能付得起房租
蒙特利尔35岁的公益组织负责人萨姆·鲁什(Sam Reusch)表示,“中产”的概念对她这一代人而言,已与父母那代完全不同。
她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学毕业,一路经历经济不稳定的成年期。虽然她小时候仍然抱有“将来能买房”的梦想,但如今她所接触的年轻人几乎都不再谈论拥有房产。
“现在的年轻人只想活得不焦虑,房租能付得起,吃得起饭,有一点点生活品质就已经不错了。”她说。
为保房产泡沫,年轻人承担代价
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、非营利组织“代际压力”(Generation Squeeze)创始人保罗·克肖(Paul Kershaw)指出,加拿大的阶层结构正在因年龄与住房而重构。
他举例说,在维多利亚市,即使是一名年收入六位数的年轻律师,也可能找不到一套合适的三居室出租屋。而几十年前用相对低价购入住房的老一辈,如今则坐拥价值百万的房产,并因此获得稳定的生活保障。
“过去25年,加拿大达成了一项‘政治协议’,那就是牺牲年轻人的经济安全,来保护老一辈在住房上积累的财富。”克肖说。
“政客们嘴上说要保护老年人的‘养老蛋’,但事实上,真正在为这些财富买单的,是正在承受高房租、被迫推迟甚至放弃购房梦想的年轻人。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活水平,为上一代人作了‘保护盾’。”
他指出,政治人物频繁强调“通胀伤害所有人”,但实际上,房价通胀使得许多房主反而更富有。他以自己的房产为例称,自20年前购入以来,房产升值已超过150万加元,“这种财富增长远超一个人日复一日辛勤工作的回报”。
虽然他理解政策制定者不愿看到房市崩盘,但也呼吁政府在制定财政计划时,应更多考虑年轻人所付出的代价。
“如果我们要拿出60亿、140亿加元减税,那至少应该补偿那些在这个体系中被彻底压垮的年轻人。”
文章来源:https://www.cbc.ca/news/canada/middle-class-voters-1.7494434